走出造型| 隋建国、刘骁纯答问录
 “文献与批评”作为“云雕塑”的理论栏目,分为“理论研究”和“讲座与论坛”两个部分,适时推出展览评论、艺术现象分析、当代艺术理论探讨等,具有新角度、新见解的学术文章。
“文献与批评”作为“云雕塑”的理论栏目,分为“理论研究”和“讲座与论坛”两个部分,适时推出展览评论、艺术现象分析、当代艺术理论探讨等,具有新角度、新见解的学术文章。
编者按:
这里推出的第二篇文字,是刘骁纯1996 年与隋建国的对谈。当时发表在 1997 年的《美术文献》上。
时间:1996 年 11 月 10 日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隋建国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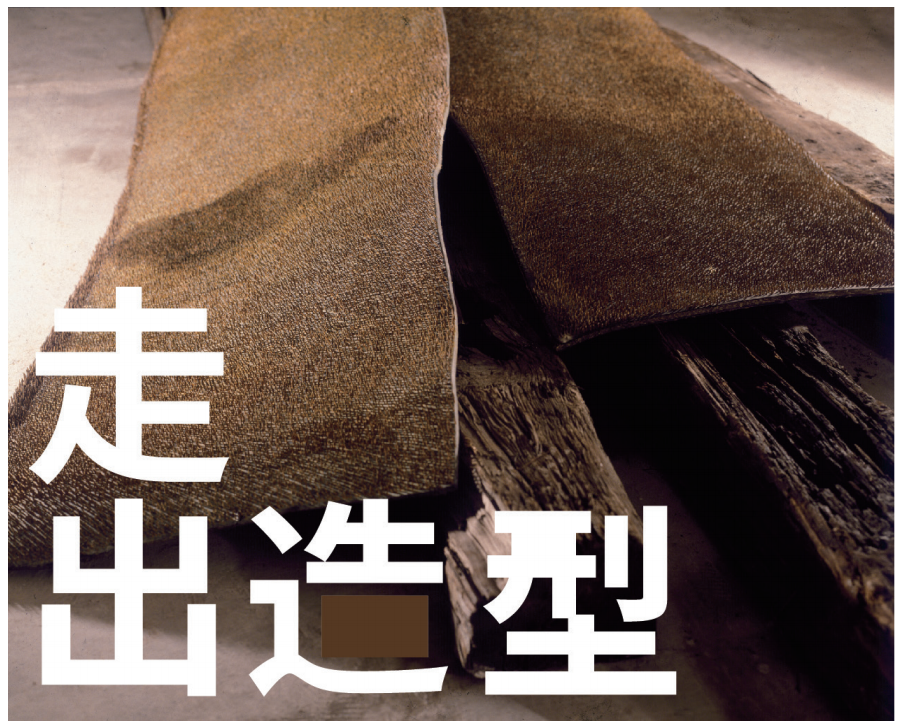
展览海报
Q:刘骁纯
A:隋建国
Q:你 1988-1989 年做的那些表现性头像,特别是那些材料感、物质感很强的卵形头做得挺棒,后来你为什么放弃了它而干起了石匠?
A:当时我正在中央美院读硕士研究生。我把那些作品叫《平衡器》系列《卫生肖像》系列,因为它是白的。当时我想,一直没有人把石膏作为最终极的材料来用,我就用铁丝、石膏、纱布,蘸着纸浆……
Q:还有直接滴淌、直接往对象上去浇石膏的方式。
A:后来作品风格越做越激烈、越来越刺激。我当时甚至想做三、四十个,用一根根竿子撑起来,摆成真人那样高,布成一个阵。
Q:除了难于展出,放弃它是否有艺术自身的考虑?
A:“新潮美术”时大家情绪很热烈,也比较浮躁。沉静下来后,我想寻找一种更沉着的、扎根更深的、把个人情绪更减弱一些的创作方式。机会很偶然。1989 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当年秋天第一个任务就是带学生下乡打石头。一打石头才发现石头的沉实、坚硬、冰冷,正好符合我当时的心情。
Q:情绪激烈、亢奋不等于浮躁,《卫生》系列也很难说浮躁,况且它本身也可以往深人发展。放弃它是否还有文化上的原因?
A:当然。80 年代初我在山东读大学时,中国文化界形成一股“寻根热”,老庄、禅宗、气功,都被翻出来,我的艺术思想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1986 年到北京之后,我对庄、禅渐渐又持批判的态度了;觉得这个东西太被动、太消极,没有对社会直接发言。
Q:那时批判传统、强调开放成为热潮。
A:1989 年之后,我开始反思,中国文化的东西又开始往外冒,觉得庄、禅式的生活态度本身也是一种对社会的发言。
Q:我一直认为经过现代转化后的庄掸精神是一种博大进取的精神,它可以成为解放中国现代、后现代艺术创造力的力量。
A:我那次下乡的 20 多天中,拿锤子东敲西打,很有感受,对生命、永恒、时间的关注突然开始敞开,找到一个切入点。感觉石头是带有生命、带有灵性的东西。
Q:这种变化似乎与你的气质也有关系,你不是那种性格十分外张、激烈的人。
A:可能。回想起来,我的艺术思路有两条线:一条比较亢奋、激烈,另一条比较沉稳、内向。近几年这两条线在慢慢靠拢,合成一个东西。
Q:你 1989 年以来这么多、这么广泛的探索大概能分成几大类或几大阶?
A:① 1990 年开始镐石头、网石头、将金属嵌入石头。到 1994 年个展,《地罣》从规模上推向一个极端,《封闭的记忆》(将岩石封入铁箱)从观念上推向一个极端。② 1994 年个展的新倾向是枕木,1994-1995 年之交在印度作了更大规模的展开。③ 1995 年初秋参与三人联合工作室,借用美院拆迁和世妇会召开创作观念艺术。④今年开始钉制橡胶板。⑤ 1992 年以来穿插做了一些借用鸟笼的作品。
Q:你为什么会对石头那么敏感?
A:如果让我找一个先行者,那就是包泡。80 年代初我到麦积山时遇到包泡。他的鼓动性很强,一路上交换了很多关于中国文化的想法,对我影响很大。他在研究了中国玉石文化以后,石雕走向了极端的单纯,让石头本身说话,走到了一个临界点上。
Q:他的这个终点成了你的起点。
A:是的。他是在石头上造形,而我不用造形。我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更大气,它可以超越造形,即所谓大象无形。我觉得石头本身已经具有了形,我承认造物主的创造力。这里,东方思维中天然去雕饰的境界与现代艺术的一些东西正好相合了。
Q:锔石、网石、嵌石,将自然造物和人工造物咬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大冲突、大和谐,极具张力,激发人们诸多的感触。这些图像的创造主要受了什么启示?
A:大的图像背景是西方现代艺术,直接启示来自生活和传统工艺中的处理手法,如镐碗、镐锅、顶针儿、金属镶嵌等。
Q:你对石雕作品的复数化发生兴趣是在什么时候?
A:1992 年我游十三陵时,受到古碑的偶然启发,回来就画出了石柱林大型户外群雕的素描草图,然后就天天想办法找人筹款,我预算是5万元一根,如果一年能立一根,立到我死也差不多成规模了。但未能取得相应的经济支持。这张素描挂在墙上两年,对我成了一种压力。后来我想,可以先从造价较低的卵石的复数化开始。于是做了四年,产生了《地罣》。我用的石头都特别坚硬、粗糙,木头也是破的、旧的,是些便宜的破烂,我可能算“垃圾艺术家”或者“贫困艺术家”。
Q:依我看,在 1994年你的个展上仅一件《封闭的记忆》就足以充满整个展示空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A:主要还是迁就场地。另外,我最初对推到这样的极端还没有充分的把握。有什么理由让人相信箱子里封了一块石头呢?做完后才发现,作品还是有说服力的。
Q:面对这件作品人们不免会发问“:这里到底有没有石头?”有石头是一种什么状态,没有石头是一种什么状态,不知道有没有或无关紧要的情况下又是一种什么状态一一这东西在观念上有一种膨胀力量,独立展示这种力量会显得更大。
A:这会逼着观者更认真地面对它。
Q:有人认为你的作品不是装置,你怎么看?
A:这不重要,关键是你想通过它说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你说清楚了吗?说得与别人不一样吗?说得有意思吗?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当你脑子里有一个装置的西方标准,然后再拼命去做装置,这就很滑稽。他们有他们的问题,咱们有咱们的问题,问题不一样,提问题的方式也应该不一样。
Q:你的雕塑有没有寓意?比如钱绍武看了你亚运村的雕塑非常激动,说这是中国文化的东西,是阴与阳的关系,又象征对抗与联合,你是否有意于这种寓意?
A:这种寓意如果带出来的话,我认为也未尝不可。但我本人没有想得那么具体。
Q:你在鸟笼中笼石头、植物、鱼,这种思路是不是网石头的展开?
A:有关系。最初我将石头放入中国式的鸟笼,做了两件,做完后发现作品说明不了很多东西,所以一直没有发表。在印度时,三个造型粗笨的旧鸟笼吸引了我,于是我把石头一块块地用水泥砌到里面,还钩了缝,把里面的空间全部填满。做完后感觉不错,感到鸟笼仍可利用,于是我又笼入鱼放到水中。笼入花养在室内。最近我发现这种方式对符号依赖太大,有点拘谨。
Q:我认为你的作品没有必要回避寓意,只是寓意宜自然、宜宽泛、宜多解、宜见仁见智。你做的鸟笼,我只喜欢你在印度做的3件,别的第一眼就容易让人想到太胶着的寓意,可展开的余地比较小。
A:是的,所以我在作“美院告别展”时就把砖砌在书架、书橱里边。
Q:这种在容器中“砌”的方式有较强的精神效应,很有意思。
A:所以我正想把“砌”拿出来发展,就是要找机会了。
Q:重新关注社会是介入三人联合工作室以后吧?
A:这可以上追到枕木墙。1994年立了50根。后来在印度又立了100根更大的枕木。
Q:旧枕木本身就可以引起人们的很多联想,你为什么不直接使用现成品?
A:是现成的上面的黑也是原有的。为了防腐,生产枕木时工厂要用高压向枕木中浸进机油,而机油吸灰吸得非常厉害。枕木使用30年就要退休,又在路边放了一二十年,所以枕木上的灰就堆得很厚·自然也就变成黑的了。我特意保留了它,一点都没动。
Q:纯粹的枕木很有震撼力,为什么你在印度做的枕木要附加许多东西?
A:如果没有这些,就等于我在印度没有得到任何感受。我将作品称为《沉积与断层》,上面嵌了许多世俗生活的现成品,如印度老百姓家里供神用的轰、灯、烙饼的锅、土著人烧的陶、有200多年历史的刻有神话传说的木雕门楣、当地博物馆收藏的美国缝纫机零件、废弃的英制机器上的商标、印度妇女缝在身上作装饰用的小镜片……这样做非常有效果。有效在什么地方呢?不在艺术家身上。纯粹的枕木,艺术家看是没问题的,但艺术家之外的人凭什么进入我的作品呢?借助这些很世俗的东西,那些普通人包括帮我工作的20多个助手和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一看就明白,能把他们自己的感受加进去。印度的一些艺术家说:“我们都没想到用这些东西”,他们觉得艺术不能用这些东西。
Q:太好了!我想,将中国的“群众路线”引入后现代艺术或许可以激发新的创造活力。
A:这促使我回国后开始挪用生活中的东西,1995年跟展望、于凡一起成立了三人联合工作室。
Q:工作室做了哪些作品?
A:实际只办了两个展览,第三个方案一直没能实现。我们的选择十分具体:中央美院9月1日搬迁,8月29日办展,我们叫“开发计划――告别美院展”。再一个就是世妇会;这两个展览时间很近,8月29日和9月15日。
Q:作品是对现实的批判吗?
A:在批判别人的时候应该先批判自己,这样,批判别人也许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我们的基本态度既非批判也非默认,而是无可奈何。我们就想把这种态度揭示出来,并固化在自己的作品中。
Q:世妇会期间的作品也是这样吗?
A:在那一年,中国许多女艺术家推出了自己的作品展。风卷全球的妇女解放运动和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仅仅是给了女艺术家、女劳模一次机会吗?于是我们就找到了最亲近的人。
Q:她们就是艺术家的妻子、母亲吧?
A:还有曾经的妻子、亲人。把她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日记、照片、活计、小礼物……陈列出来,她们本人也到场。这里有劳动模范·也有最普通的工人,还有出过国、留过洋的现代青年。
Q:这是中国妇女的普通细胞,秘密性中折射着普遍性。我看作品时十分感动。
A:题为“女人,现场”。在英文中,现场即此在、此岸、现实。
Q:你们的布展为什么搞得那么精致?
A:建国几十年来,从博物馆到工厂、街道,乡镇的宣传栏,展示的都是英雄模范,而且基本形式不变。我们一本正经地挪用这种流行形式,一本正经地把一个个普通人当成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对待,这样才可能引起观众思考。
Q:在艺术观念上你们有什么考虑?
A:我们想看看新的可能性。如果把这件事当成艺术来做时就容易进入已有的标准体系――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这就不会有新的可能性。因此就要做得不符合艺术,不把它当作艺术而当成一件工作任务丢认真完成,或许就会有新的东西生发出来。这是反证法。
Q:第三方案是怎样的?
A: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王府井要变成更繁荣的商业区,因此要把校尉胡同拓宽成大马路。路东边是协和医院,西边是美院画廊。医院又比画廊重要,于是只能把画廊拆掉。我们计划在拆之前在画廊中铺上马路,有便道有车道,完全是对马路设计蓝图的提前施工,让大家进入画廊后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仿佛站在马路上。我们不得不面对画廊与马路、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尴尬。画廊至今没有拆,这个事情也就没能做。
Q:在美院拆迁的作品中,大家了解最多的是喷上红颜色的石膏人体习作,你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式?
A:这是机遇。学校搬迁时雕塑很难搬运,于是学校下令每个学生只许带走3件。当教室搬空后,看着到处躺着被学生扔掉的人体习作,我感到它们特别能代表美术学府的形象。人体艺术早在古希腊就开始了,我拿它来说事就可以说得很多、很深。人体习作放在那儿,我很容易判断哪些学生做得好,哪些学生做得不好;可是当我把它们喷上红漆时,发现好与不好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揭示出学院那种过分细微、精致的技术追求到底有多大意义?
Q:为什么要涂成红色?又为什么要描眉画目?
A:开始设计的是肉色,后来发现还是红的好;开始颜色也没有那么红,可在喷涂的过程中发现还是越红越好,于是就干脆用纯粹的桃红。结果发现这种艳俗的红才是最有效的。当描上眉毛、睫毛、嘴唇、指甲时,它与桃红的配合就更有意思了。它标示了当今艺术某种很尴尬、很媚俗的状态。无论是前卫艺术或非前卫艺术,连我们自己在内,都在作出各种媚俗的姿态。
Q:这是一种应激的、偶发的、回应社会事件的艺术创作,它自身已是事件,它的文化性格没有波伊斯那种强烈的扩张主义·它是静观中的内敛中的外张,撼人却不伤人。被动的,创造则是主动的。
A:这些事件的确不那么张扬,我由此进一步认识自己一贯的艺术状态。这种状态关系到我现在新的作品钉制胶板。
Q: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A:实际是为今年年底将在北京举办的学术邀请展准备作品时被逼出来的。中国美术馆二楼无法搬运进大石头展出,可我又不能再用小的石头了,我不愿意重复自己。我想起以前的某些试验,比如利用箱子、桌子、椅子等,如果钉满钉子,表面全是钉子头,钉子帽什么的,那肯定是挺奇怪的感觉。可是真正做的时候发现行不通,假设一个木头上面计划钉1000个钉子,可是到钉了600个的时候,木头己经烂了、粉粹了,不能再钉了。木头的承受力不行。
Q:因此便选择了更具韧性的橡胶材料?
A:是的。我先找一小块橡胶作试验,没想到这块小胶皮钉满钉子也毫无问题。我发现,因为承受,它变了它从一个承受的、被动的东西,变成了挑衅的、主动的东西。钉子已经与橡胶合为一体,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规模越大,这种感觉就越强烈。
Q:你的作品总离不开对承受力的关注。
A:是的。近百年来,中国人的承受力很强,非常有韧性、善于生存,包括我自己。
Q:从打石头以来你的全部作品的精神状态的确有一个统一的脉络。这种脉络可以说是精神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古典现实主义的某些精神,如:在特殊中蕴涵一般、在偶然中蕴涵普遍、作者态度含而不露地寓于深刻有力的现实剖视之中等等,在新的意义上被重新激活。你的作品最让人颤栗处大概就在于你目不转睛地死盯住了人们总想避开的带普遍性的精神现实,常能激起人们十分复杂的感动。
钢筋在网住岩石的同时又不能不顺应岩石,岩石在被箍扎的同时又迫使钢筋服从自己的形象;被水泥筑在一起的石块砖块在堵塞岛笼、抽屉、书橱的空间的同时又被异己的笼、屉所堵截,笼、屉在限制石头的自由的同时又被石头夺去了自己的自由空间;当铁钉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穿透能力、橡胶板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的同时,双方原有的一切优势便同归于尽。人体可作作为学院艺术的骄傲,在它获得最耀眼的色彩的同时,便失去了它的全部骄傲……这一切都可以视为生命在物质化的过程中的消耗和展开。物化对象中既寄寓着灵魂的无奈,又显示着灵魂的坚韧,并在不断迸发的想象力中完成着灵魂的超越。
发表于《美术文献》总第 8辑 1997年
【完】
关于作者

刘骁纯(1941年3月-2020年6月),196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艺术理论家、批评家。1973年至1979年,在陕西省群众艺术馆任美术组的美术干部。历任《中国美术报》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学委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2020年6月30日于深圳去世。

隋建国,1956 “在中国当代艺术观念上走的最早和最远的雕塑家。”(黄专语) 年生于青岛,雕塑家,中央美术学院资深教授,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排版:郑彭艺
编辑:金龙
审校:琴嘎
资料提供:北京隋建国艺术基金会
官方网站:http://www.suijianguo.org.cn
官方微博:北京隋建国艺术基金会
官方微信公众号:云雕塑Cloudsculpture
雅昌艺术头条:云雕塑
邮箱:safyun@qq.com
*以上所有图片、文字、视频素材,由受访人和机构惠允和授权使用,未经基金会授权不得转载。
